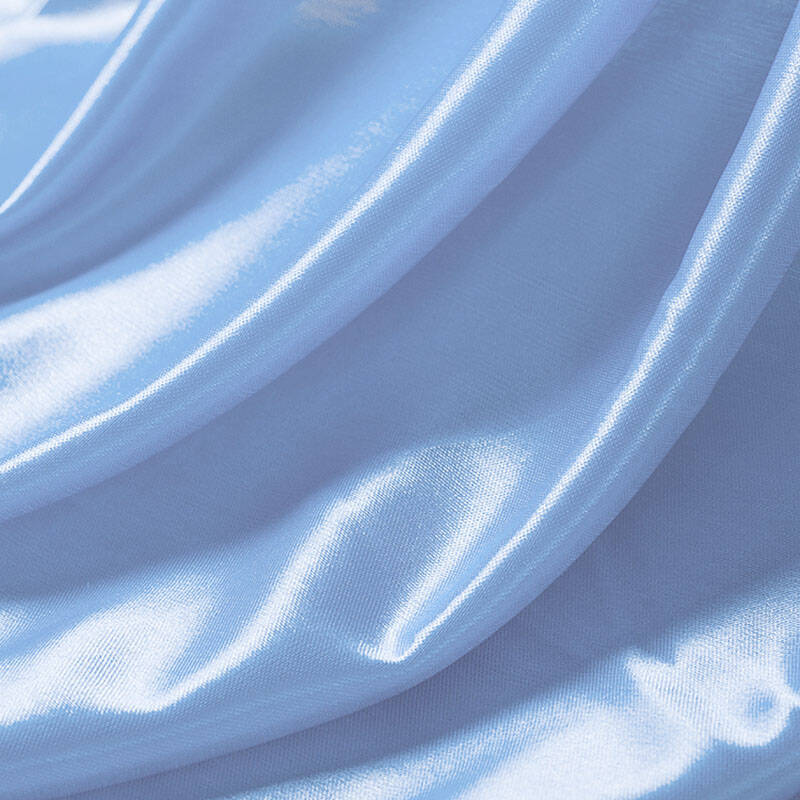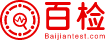大姐夫回老家种
棉花,有我太多温暖的记忆。想到儿时母亲在灯下做棉鞋,她把棉絮缝在鞋面里,一针一线密密地缝呀缝;想到母亲为我们兄弟姐妹轮流做棉袄,她总是边做边说:“十层单,比不了一层棉。有了棉花才能过冬啊!”那时,一到冬天,身上穿的几乎全和棉花有关:棉帽,棉裤,棉袄,棉鞋,就连缝衣服的线,也是用纺车纺出来的。
家里兄弟姐妹多,每个人的棉衣、棉裤、棉鞋都需要棉花,所以每年春天,母亲总要带着姐姐们种棉花。当时的我还小,只是个小跟班。记忆中,春天种下棉花籽,之后侍弄非常精细,需不断地拔草,还要打叉,希望棉花多结棉桃。打完叉的棉枝迅速庞大起来,像一棵棵树。一眼望去,整个棉地像一片茂盛的树林,苍翠、浓郁。
棉花的花,单薄的花瓣,繁密的筋络,由花心向边缘散开,细细碎碎的花粉粘在花瓣上。初生的花是浅黄娇嫩的,随之会被日光晒成深红色,像一只只美丽的蝴蝶,翩飞在这绿色的海洋上,美得让人心醉。然而,*亮丽的景色要数铺天盖地、缀满枝头的棉桃,一个个像熟透的桃子,鲜艳又芬芳,爆出耀眼的丰硕。
秋天,棉花绽开了笑脸,我总是跟着姐姐去地里摘棉花。印象中的棉花,开得白,朵也大,也许是人小手也小的缘故。都说秋高气爽,可记忆里摘棉的日子永远是“秋老虎”。日头毒辣辣地照在头顶,我们戴了草帽低着头,为防划破皮肤,穿了长衣长裤,汗水像雨水一样淌下来。棉花枝叶滑到裸露的脸上,钻心地疼痛。可是,抬抬头,望一望白花花的棉花地,劳累便被喜悦代替,因为冬天就有新棉袄了。
秋末,霜打的棉花秆再也挺不直腰,叶子都耷拉了脑袋,于是被拔了回家。靠在向阳的南墙根底下,青桃在秋末的阳光里慢慢绽开。母亲会在白天里把稍绽开的棉桃摘下来,晚上在煤油灯下,一颗一颗剥开。那时,晒干的棉花秆又可以当柴烧。
由于当时买布都要布票,母亲就每年轮流给我们做棉袄,一件要穿两三年。记忆中,我*喜欢的那件红底黑点的棉袄一直不舍得换掉,足足穿了四年。
棉花里,留存着我*温暖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