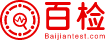一直盖着的丝棉秋被越来越显示出单薄的本性来,让我从夜半的酣睡中冻醒。想起母亲从家乡送来的温暖
这一招真灵,电话打完几天之后的上午,我收到了来自家乡母亲寄来的包裹。手忙脚乱地剪开蛇皮口袋的邮包,棉被终于露出了本来的面貌——紫色的被面,上面描着银色的小花,白色的被里,两头包裹着紫色的枕头套。下午母亲就打电话过来追问棉被收到没有,还特地了解物流输送过程中被子是否淋湿,即使没有受潮也一定要先彻底晒干后再用。
晚上,盖上棉被,有一股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夹杂着我的童年和少年,唤起了我许许多多的记忆。这种被子在城市的专卖店是买不到的,现在的年轻人热衷于使用各类时髦的羊毛被、蚕丝被、羽绒被,它们轻巧蓬松,色彩亮丽,蕴含着一种激情,一种雅致的生活;而我的棉被则不同,它笨重、朴实,散发出
在我们湖南老家,棉花是主要的经济作物,一个农民一年甚至一生都在和棉花进行着各式各样的交道。从我记事起,每到春耕前后,父母就要下田翻地,为即将开始的种植棉花做准备了。布谷鸟欢快地叫着,农民开始了伺弄营养钵,刚刚放学的我们,小小的布书包挂在屁股后面,手里拿着棉花种子,一个坑一个坑地点着棉花种子,往往半天以后站了起来,眼冒金花,几欲昏厥了。随后还有移苗、理枝、除虫、扶根,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的活,每每是放学以后,不情愿地被父母赶到了田里,只能替他们分担一些微不足道的活计。到了秋天,漫野的棉花都咧开了白色的笑脸,真正的农忙时节就到来了,父母们没日没夜地在田里采摘棉花,害怕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让花色变黑,卖不到好价钱。长长的田垄似乎看不到头,我们跟在父母的后面,拣着低矮的、大人得费力弯腰才能够到的棉花。等到完全黑了天,父母才迈动疲惫的身躯,背着重重的棉花包,一步步走回家去,然后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挑拣出花里面的败叶。而那时矮小的我,就要踮着脚尖,淘米进锅煮饭。吃了晚饭,带着弟妹们早早地钻进被窝里,半夜小解的时候,看到灯光下,父母还佝偻着身体忙碌着。
等到收完了棉花,晒好,紧紧地塞进棉花包里面,就要去合作社的收花店卖棉花了。父母亲拖着的板车上堆着高高的花包,我和弟弟就跟在后面,蹦蹦跳跳地走着,幻想着供销社的冰棒和汽水。来到收花店,一个肥硕的质检员拿着尖尖的探针,戳进花包里面,然后再抽了出来,评定棉花的级别,再过磅、记秤,*后把棉花推进花仓,倒进堆积成山的棉花堆上面。每次评完级,善良的母亲总要嘟哝几句,你爹也不去找找人,每次我家的棉花级别评得*低。那时童年的我哪里懂得父母的艰辛,看着那个质检员撕下了一张白条,就吵着要吃零食。轮到回家了,我和弟弟在前面走着,争论着谁喝汽水谁吃冰棒的问题;父母亲在后面依旧拖着板车,迈着沉重的步伐,想着揣进兜里的那张白条,计算着这年有限的收成,品尝着生活的艰辛。
母亲有个习惯,并不是所有的棉花都拿去出售,总有一些优质的会留下来自用或送给亲人。等到农闲时刻,走村串乡的手艺人会背着长长的弓弦找上门来,专门给各家做被子里的
按照我们老家的规矩,新嫁的女子,娘家都是要陪上几条新被子作为嫁妆的,寓意在于希望子孙后代有暖和的被子盖,免得忍冻挨饿。在妹妹准备嫁人的前几周,那时候我已经在云南当兵、弟弟也在上海参加工作多年了,我们兄弟俩特地陪母亲一起进城到大商场挑选几条好被面。母亲明显老了,岁月在她的身体上留下深深的痕迹,步伐也有些踉跄。我扶着母亲,一家家地仔细挑着,找到适合的被面。母亲用手抚摸着那些光滑的绸缎,是否也在惆怅自己作为新嫁娘的时候,没有能够用上这样的面料?那时的母亲,已经看不清针眼、穿不进针线了,这些准备工作都是我完成的,母亲勾被时的手也不停颤抖。我总是劝说母亲去买一些新潮的被套,省去了很多手工的烦恼,她不但不听劝,在我们兄弟俩结婚和孩子出生时,还亲手缝制棉被送来,因为母亲坚信,只有用她种的棉花一针一线勾出来的被子,才足够温暖耐用。
收到家里寄来的棉被,往事如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中掠过。这些对于我的妻儿来讲,都是遥远而陌生的生活,但是于我,却有不同的意义。那些父母吃过的苦,那些朴素而笨拙的传统,让我始终能坦然面对军营艰苦生活的磨砺。
寒夜,我在母亲亲手缝制的棉被里安然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