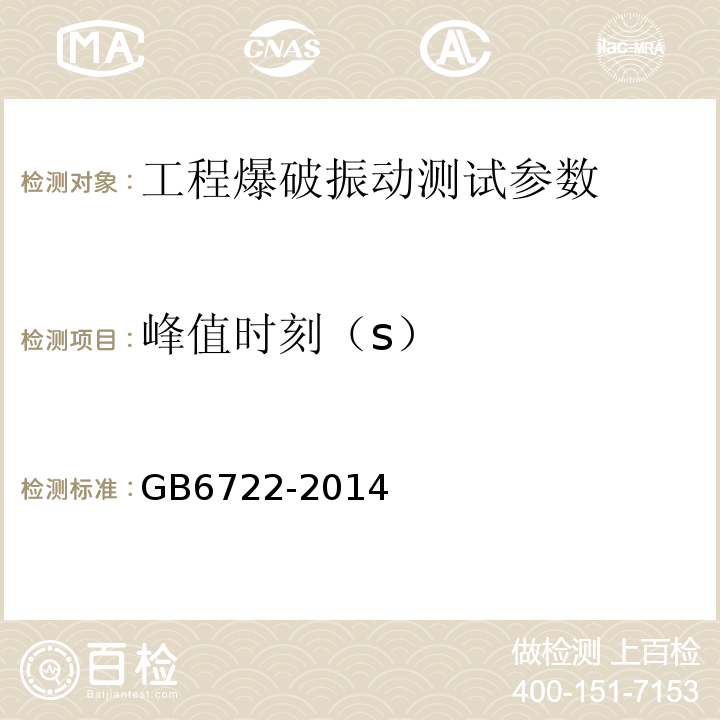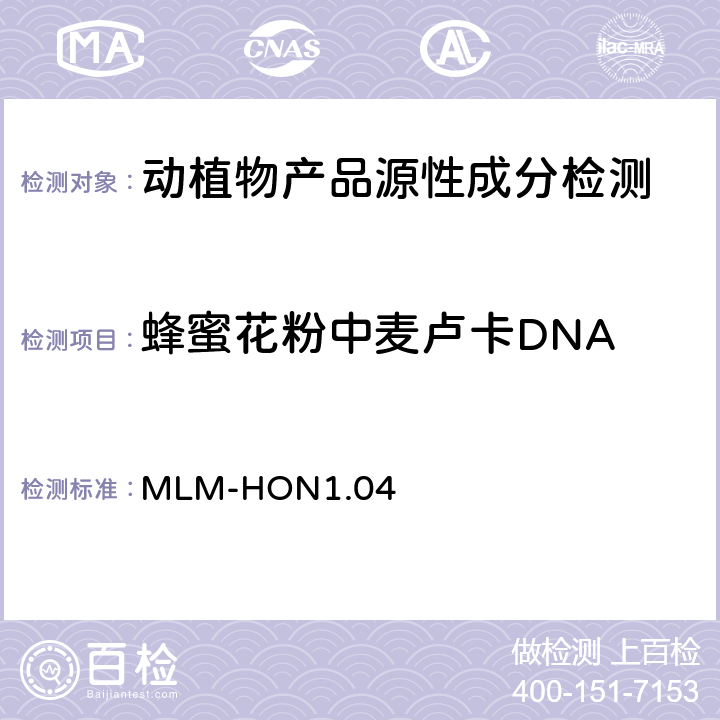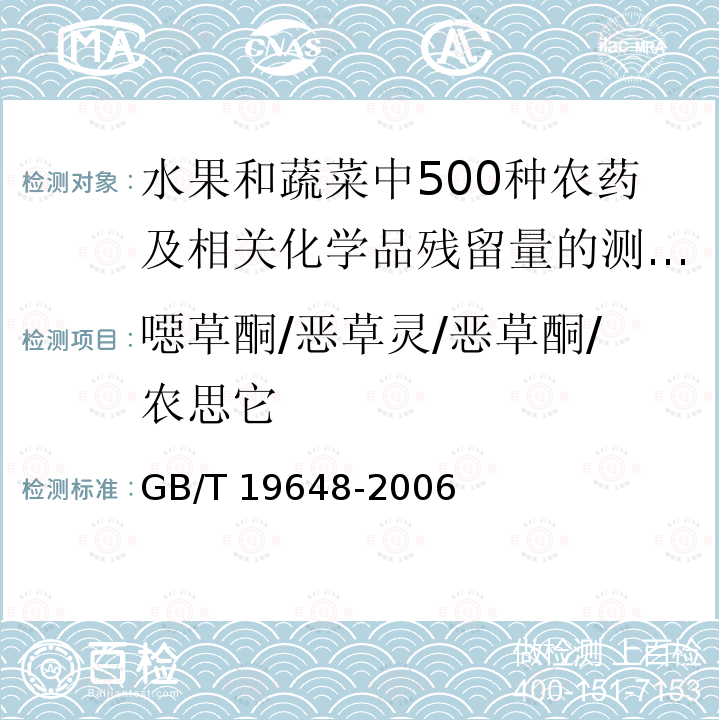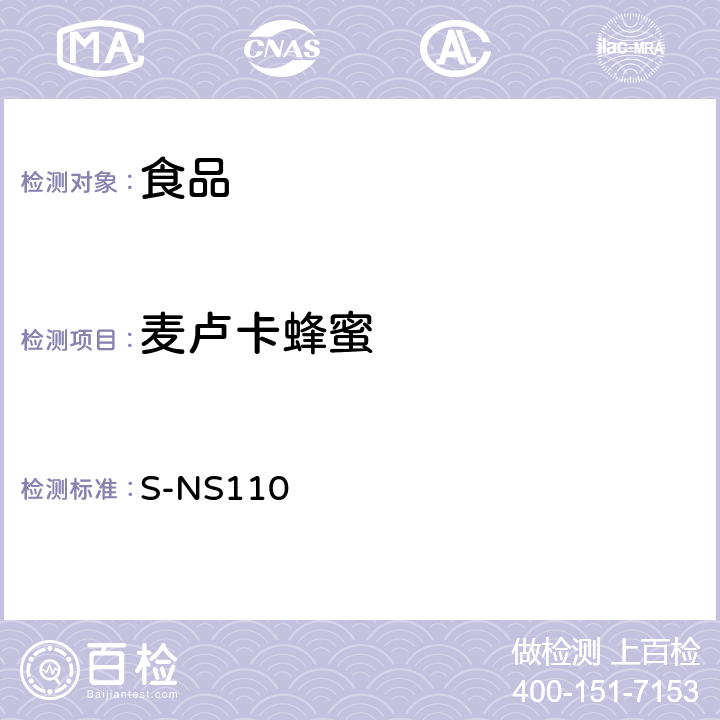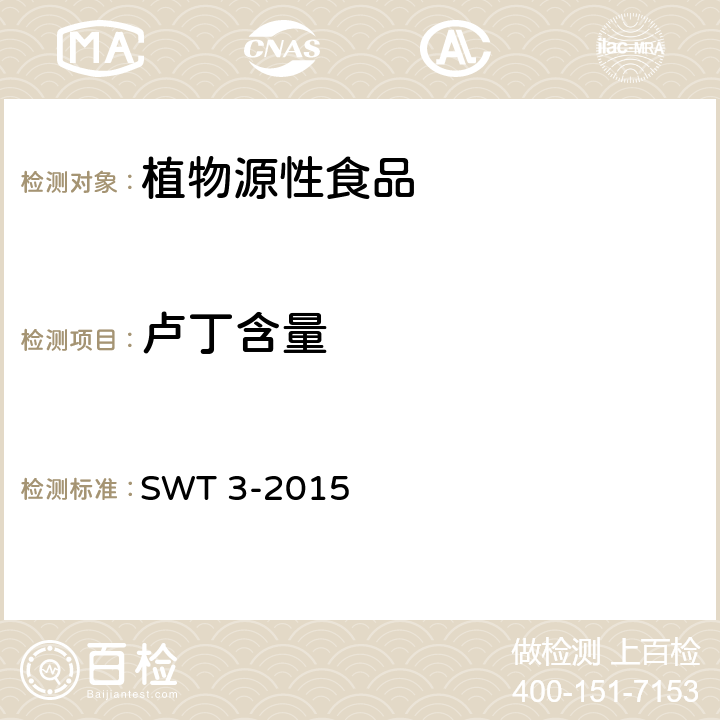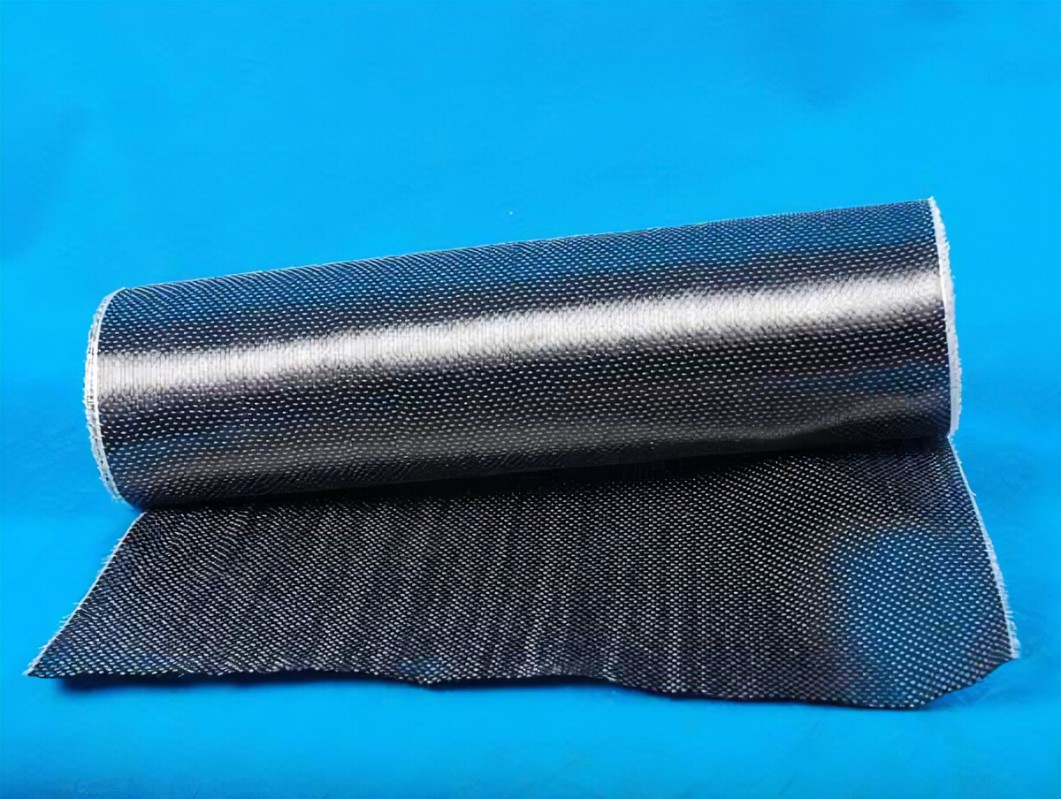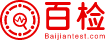生机转瞬即逝,而且很可能就在我们这一代的踌躇彷徨中溜走。大多数人不知道,也许是不在乎,人类文明原来随时会毁灭
本刊记者 彭苏 实习记者 任明远
发自北京
152 0173 3840年9月15日,加拿大温哥华的清晨,3个小伙子登上了一艘名为“菲莉丝·科马克”号的小船。
他们按计划驶往北冰洋上的阿姆奇特卡岛,对美国政府将在那儿爆炸一枚100万吨级的氢弹,表达他们的强烈抗议。
至此,“绿色和平”这一全球性NGO,正式踏上了国际舞台。
“现在绿色和平的总部设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全球40多个国家设有办事处。共有2000多个工作人员,300多万名志愿者。”通往温哥华的电话那厢,绿色和平(中国)总监卢思骋用港式普通话温和地作起了介绍。
NGO生存的空间会越来越大
2001年,卢思骋从香港单枪匹马,先后到达广州与北京,成立了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的分支。
这一年,没有助手,没有正式像样的办公室,绿色和平(中国)就他一人在做事。
扎根大陆之前,他是香港中文大学活跃的社会活动分子,颇具环保、劳工、社区、学校民主化等各种社会运动的经验;他曾主修和平与冲突研究,研读过人类学硕士课程;自认为熟谙中国现代历史发展及马克思哲学,深刻认识“在中国做任何社会工作时,政府的重要性”。
但他仍要面对——“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对NGO组织一直实行灰色地带管理方法。即实行‘不取缔,不承认,不认可’的‘三不政策’。”
刚到北京时,有媒体呼吁要谨防西方某些非官方组织,小心他们在中国搞“天鹅绒革命”。别说政府官员不愿接见他,“哪怕是环保研究领域的朋友,都觉得我们来会把他们污染了。”卢思骋说。
出于某种竞争意识,本土NGO也不会朝他展开欢迎的双臂。
由于国际NGO组织尚处于“暧昧”地位,绿色和平(中国)必须与具有合法身份的机构合作,从一个个具体项目做起,慢慢壮大存活。
卢思骋仍然记得,在当年深思而就的3年计划书中,他写道:“我觉得中国的环境问题只会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恶化。政府会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NGO生存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大。对绿色和平来讲,我们怎么样能够不浮躁地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
非法转基因大米调查,是绿色和平(中国)做的**个也是*复杂的一个项目。
2005年,当它首次对外公布调查结果时,很多NGO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
卢思骋的考虑是:选择它有多重原因。**、事关粮食,就不得不引起政府的重视;第二、它不敏感,2001年时转基因食品问题就已在国际社会引起讨论;第三、可以通过做响这一项目,对外渗透我们的做事风格,同时也为媒体提供充分完备的材料,让记者写出深具威力的内容,取得媒体的信任。
在他随后转发的一份材料中,我们看到,2005年年初——
在湖北的一个小餐馆里,朋友介绍的一位业内人士带来很多新种子的广告。一个来自松滋县的抗虫稻推销广告,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当时调查人员几个电话打过去,才要到了一个当地农技站的人的手机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对方在电话里告诉调查人员车号,让他在松滋汽车站暗中接头。
见面时,坐在车里的是个精明的中年人,货就在座位下。他打开两个袋子让调查人员验货,里面每个小包装袋上并没有标明抗虫稻的字样。
我们的人说,这样的东西拿回去无法报销,对方在发票上写着:因为国家法律问题,不能在包装上注明是抗虫稻。
为了保证调查的准确,录音、录像、文字、图片等相关证据要完整保存,每次我们的调查都要两人同行。获得的证据不敢放在身边。发票、种子、采集的样本,要快递回北京。声音资料也尽快整理成文字,并在**时间发送到安全的地方。因为要时刻准备着对付不测。
**次送到德国做基因检测的25个样本,大部分也是调查人员在武汉两家大粮油批发市场采样得来。
那一次的调查报告,一时间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热点,“我们通过调查指出,目前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品种涉及多项国外专利,一旦中国通过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审批,将为国外生物公司打开大门,他们可以通过收取专利费等手段来控制中国主粮,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