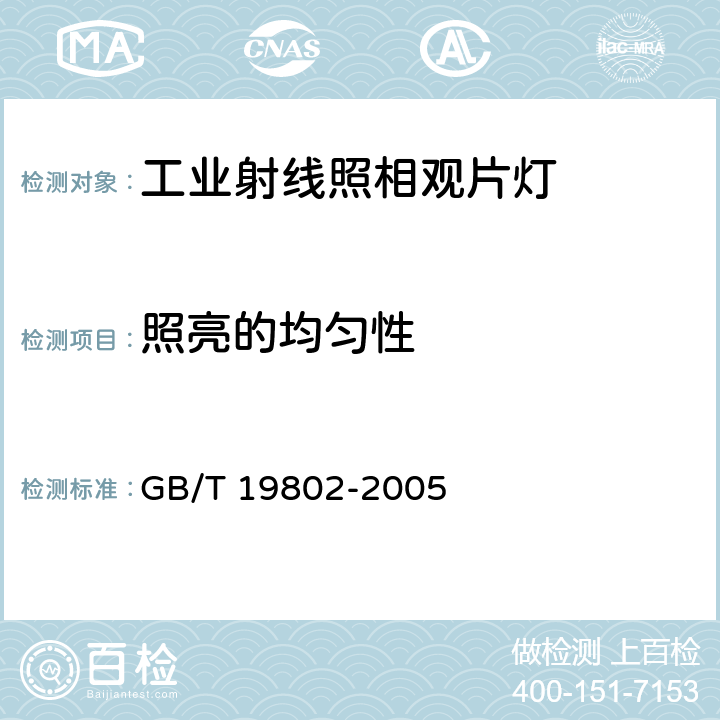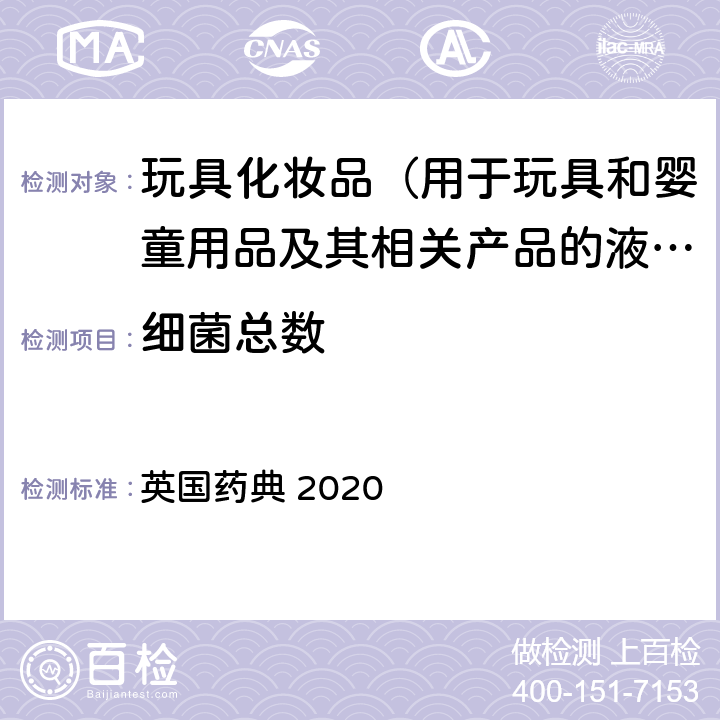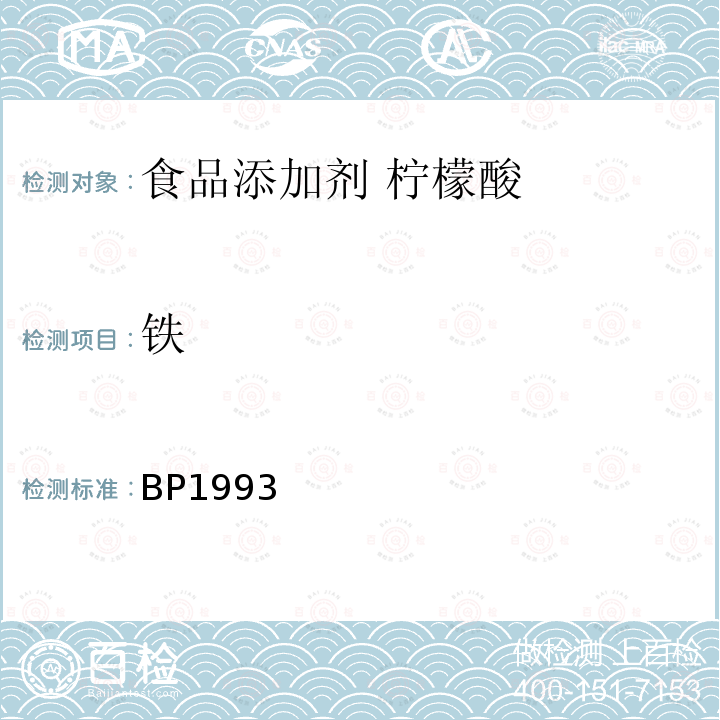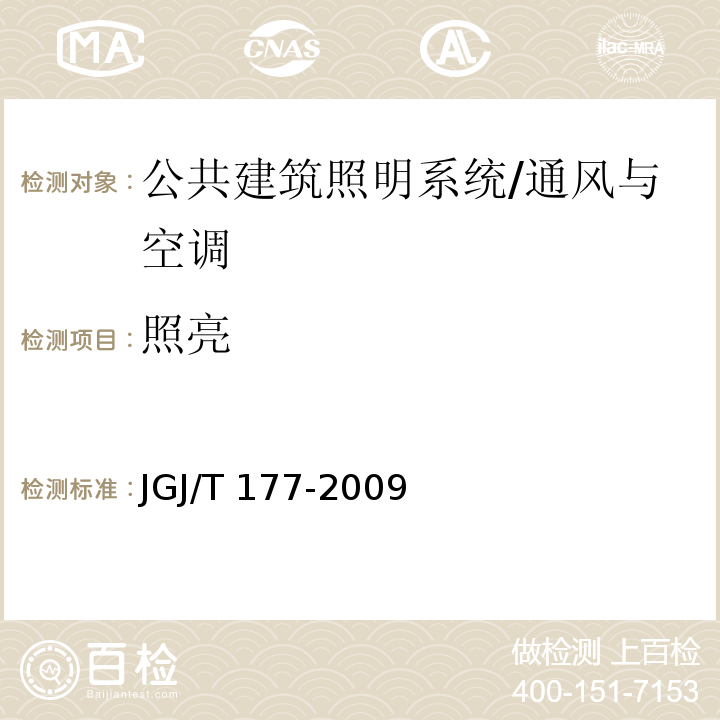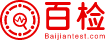【观察者网前几日发布了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文一的文章《中国为何超越 因为中国找到了工业革命的“秘诀”》,引起读者朋友们热烈回应,不过也有读者提意见,认为文章忽略了前三十年中国工业化的成就。
文一教授特别回应说,他即将出版的新书《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在很多地方讨论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读者只有通读全书对中国崛起和工业革命本身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才能够真正对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辩证关系以及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还讨论了腐败问题,和为什么只有工业化(即第二次工业革命)顺利推进并接近完成的国家,才有能力真正反腐,并把腐败控制在不至于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程度。
中国作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突然出现在地平线上,震撼了世界。甚至直到十几年前(也就是大约156 0190 260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还很少有人敢预测中国能够迅速成为一个区域性工业强国,更别说全球性超级经济大国。
事实上,很多人都在不断打赌中国的崩溃,频频引用“八九”风波、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经济大衰退(它使中国出口与过去增长趋势相比几乎永久性地削减了40%)作为证据。但现实一再无情地反驳了这些悲观的预测:
随着35年的超高速增长,中国走来了(came)、见证了(saw)、征服了(conquered)—— 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创造了比她过去5000年所有朝代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的生产力,从一个*度贫穷的、人均收入仅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水平三分之一的农业国转变为世界上*大和*具活力的制造业强国。1
例如,中国当前用低于世界6%的水资源和9%的耕地,一年能生产500亿件T恤衫(超过世界人口的7倍),100亿双鞋,8亿吨粗钢(世界供给量的50%,美国水平的9倍),2.4亿吨水泥(几乎是世界总产量的60%),接近40亿吨的煤(几乎与世界其余地方的总量相同),超过2200万辆汽车(超过世界总供给量的1/4),和62000个工业专利申请(美国的1.5倍,超过美、日总和)。
中国也是世界上*大的船舶、高速列车、隧道、桥梁、公路、手机、计算机、自行车、摩托车、空调、冰箱、洗衣机、家具、纺织品、玩具、化肥、农作物、猪肉、鱼、蛋、棉花、铜、铝、书籍、杂志、电视节目,甚至大学生等产品的制造者。
一句话,承受用全球*少的自然资源养活世界20%人口的压力,中国却能提供全球1/3的主要农产品和接近一半的主要工业产品。中国实际GDP自1978年以来30倍的惊人扩张的确令人意外。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过去几百年的无休止的动荡、衰竭与内忧外患,还因为它那经久不衰的集权政治制度——按照制度经济学理论,这种“榨取性”的“专制”制度不可能导致一国工业化的成功。2
但这种理论过度美化了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和它的经济功能,却忽视了西方列强自己当年亲身走过的那段并不那么光彩的发展道路。
通过假设先进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这些理论忽视了制度和法律在人类历史上由生产方式推动的内生性演化,以及在任何政体下面口号与实践之间、法律与执行之间、制度与政策之间的不连续性和不相干性;从而导致对后果与原因、相关性与因果性、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开放的政治权力与开明的经济自由之间的混淆。
*重要的是,他们忽视了以下根本事实: 普选民主是工业革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现代西方法律制度与实施它们的巨大组织动员能力是西方几百年基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重商主义、奴隶贩卖和带血的原始积累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产物。3
这种因果关系的混淆在一个方面解释了西方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推广西式民主的巨大热情,而不顾其初始的经济、社会、政治条件。4 这种从政治上自上而下的发展经济的方法所产生的结果已经十分明显。
看看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和利比亚的经济停滞与持续的政治动荡,以及在乌克兰和东欧其他地区所产生的结果: 高调的民主出现了却又随之崩溃,生活水平提高了却又随之倒退,繁荣的希望升起了却又随之破灭。如此无休止的恶性循环成了这些不幸国家和人民的“新常态”。5
因此,尽管《国富论》出版已将近250年,尽管那么多的笔墨已经挥洒在经济增长的一般均衡模型上,当代经济学家们仍然在黑暗中探索经济发展的秘密——那个神秘的能启动企业组织爆发式增长的“双螺旋”自我复制机制。
亚当·斯密其实比他那些现代新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们,更接近于发现这个秘密。他用18世纪早期别针制造厂的例子,和基于市场规模的劳动分工原理来解释国民财富增长的秘密。
但他那些现代新自由主义的学生们却误将民主等价于市场,市场等价于产权,产权等价于激励。
他们似乎断言:只要有了民主,即便没有大航海与美洲的发现,没有英国对全球纺织品和棉花市场的垄断,没有它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获取的巨大财富,没有它在殖民和开辟全球市场时所依赖的强大国家机器,以及对类似东印度公司的全球商业利益和垄断势力强大的军事保护,英国工业革命仍然可以发生。6
在经济学的另一个*端,单纯建立在边际分析和资源分配基础上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虽然数学优美,却仍然面临如何从微观个体理性选择出发,来推导出国家层面工业革命和长期经济增长的艰巨挑战。
怎么能够让原始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只关心个人利益的小农个体,在给定收入下通过选择效用*大化的消费品,来使欧洲列强突然在19世纪逃脱马尔萨斯陷阱,并产生****的科技和产业革命?
在这类抽象的增长模型中,不仅国家多余、政府多余、意识形态多余、工业组织多余,而且市场和它的创造者自古、自然、自动存在,以至于只要在抽象的生产函数中假设相同的资本份额,那么20世纪的福特汽车装配线,与18世纪的纺织作坊对于经济和工业组织的意义就是一回事7。
难怪技术进步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只是一个“黑箱子”。难怪“索洛残差”(Solow Residual)所测量的只不过是我们的无知。难怪250年前**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仍然是一个人类历史上*大的未解之谜。
即使对于博学的经济史学家们,工业革命也太让人费解,甚至觉得无解。它至多被认为是一种只能被那些“命中注定”、拥有得天独厚地理条件和神秘文化基因、少数“准西方”国家所能理解、“只能意会不可言喻”的一种特殊的“知识”。
因此,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2012)无可奈何地哀叹: “解释工业革命仍是经济史上的**大奖。它到目前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穷其一生,但总是无果而终。”
但中国却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重新发现了这个“只能意会不可言喻”的知识——工业革命的“秘方”。这个事实几乎完全不被西方学术界和媒体所洞察。因此,我们才看到西方(甚至好多中国人自己)对中国迅雷不及掩耳之崛起的*度迷惑和严重低估,和由此而滋生的恐惧、怀疑与偏见。
以工业化的年历表来看,中国早已在1978年改革后*初的15~20年的乡镇企业繁荣中,成功完成了**次工业革命;并在1990年代末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目前已经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和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门口——尽管一直充满成长的“烦恼”。
对于习惯于西方中心论思维的中外学者和媒体来说,这一切都似乎是中国政府靠海量投资堆积出来的“振兴假象”,靠牺牲环境和百姓利益而炮制的一个巨大的、随时可能破灭的经济泡沫。
其实,这一切不过是所有老牌工业化国家都曾经历过的“工业革命”。它静悄悄地爆发,像无声的热核反应一样,把一切对中国行将崩溃的悲观预言,无情地吞噬在其迅速蔓延的冲击波和蘑菇云中。8
到底什么是工业革命?为什么它在中国缺席和推迟了200多年?却又在十年“文革”摧毁了本已稀缺的人力资本和商业基因之后突然被成功引爆?地理、产权、制度、法律、文化、宗教、资源、科学、技术、民主、教育、国际贸易、产业政策、重商主义、政府权力、国家意志等等在工业化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实现快速的工业化有捷径吗?印度、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国家能否效仿中国的成功,在21世纪引爆它们自己的工业革命?9
中国对工业化的执着与锲而不舍的历次尝试
工业革命似乎是一个戏剧性的社会经济迅速变化的神秘过程。这个过程,少数西方国家(占世界人口的一小部分)在18、19世纪经历过;多数落后国家(超过世界人口的90%)在20世纪渴望效仿但不断地惨败。对于这一神秘过程,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仍在孜孜不倦地费力理解和寻找答案。10
但在过去的35年中,如果任何具备敏锐观测力的西方人能够每年去中国哪怕一次,摘掉欧洲中心观的眼镜,他将发现“神秘”的工业革命就活生生地展现在他眼前,看得见,摸得着。
中国至少把英国在1700—1900年,美国在1760—1920年,以及日本在1850—1960年所经历的革命性经济变革浓缩到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
西方观察员会在中国看到亚当·斯密(1723—1790)、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大卫·李嘉图(1772—1823)、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卡尔·马克思(1818—1883)和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的思想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由超过10亿活生生的中国人生动地演绎和再现着——目睹那数以亿计的组织起来的农民工、纺织工、矿工、铁路工、商人、企业家、投机商、套利者、创新者、国家机关和有商业头脑的政府官员们。
他们都穿着中式服装,因此在西方观察员看来显得陌生和异类。然而当下的中国或许比19~20世纪的西方列强更加善于演出“资本主义”这出大戏。
在政府主导的重商主义与市场竞争的有机结合下,在没有任何“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橙色革命”、“茉莉花革命”或“阿拉伯之春”的光环下,邓小平先生和他的继任者们已经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创造性毁灭”精神转化为中国新纪元的**精神(引用黑格尔),并且是在西方学者所谓“榨取性”的政治制度下实现的。11
但“资本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D.麦克洛斯基的“小资产阶级尊严”和致富冲动),还是一个崭新的信念和思想体系(J.莫基尔的“开明经济”),或一种新的工作道德(M.韦伯的禁欲新教),一种新形式的国家政权与社会秩序(塞穆尔·亨廷顿),或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卡尔·马克思)?
当如此多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沉浸于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200多年前的英国,而不是欧洲其他国家,或18世纪的中国或印度时,却很少有人问一问,尽管有足够多的机会和后发优势效仿英国工业化,为什么中国和印度在其后200年的时间里仍然没能实现工业革命?这个问题难道不是同样甚至更加有意义?
换句话说,通过问为什么印度现在还没实现工业化,我们可能发现工业革命当年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印度的根本原因。缺乏民主和私有产权显然不是答案: 印度几十年来一直是*大的民主国家,也是全球私有财产历史*悠久的国家之一。
棉纺织业的比较优势在18世纪从印度向英国的转移(Broadberry 和Gupta, 2009)也不是印度无法开启工业革命的原因: 印度有200年的时间观察、学习和效仿英国,并夺回她的比较优势,就像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终做到的那样(中国在1995年成为世界上*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
为什么英国式的工业革命没有在其他国家发生?缺乏民主和私有产权显然不是答案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研究者们倾向于问,为什么在17、18世纪,拥有**纺织、炼铁技术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市场繁荣经济的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参考“李约瑟之谜”的大量文献与*近彭慕兰(K. Pomeranz,2001)关于东西方“大分流”的著作。对于“大分流”问题的争论和介绍性文献,可参阅Bishnupriya Gupta and Debin Ma (2010),“Europe in an Asian Mirror: the Great Divergence”,和Loren Brandt, Debin Ma and Thomas G. Rawski (2012),“From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 Re-evaluating the History behind China’s Economic Boom”。)
而不问一问为什么在几百年后的20世纪中国依然贫穷,无法实现工业化?简单地把工业化失败归咎于精英阶层的既得利益保护和榨取性制度(如制度学派所深信不疑的),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甚至是误人子弟的。12
需要指出,中国1978年开启的经济改革并不是中国在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黄土地上**次雄心勃勃地尝试启动工业化。这是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的120年间中国第四次工业化尝试。
中国**次尝试发生在1861-1911年,也就是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击败之后。中英进行了两次鸦片战争(分别在1840年与1860年左右)。
在两次战争中,英国依靠其强大的海军力量,摧毁了中国禁止从英印度进口鸦片的努力。英国输出鸦片是为了平衡其由进口中国丝绸、茶叶造成的巨额贸易逆差和银储备损失。
因为没有工业化,中国两次战争都失败了。在20世纪末,工业化的美国靠超级军事实力和国家渗透赢得对拉美毒贩的战争,成为历史上**赢得国际有组织贩毒(鸦片贸易)战争的国家。晚清政府被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深深侮辱,开始了一项使落后农业经济现代化的雄心勃勃计划,包括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海军与工业体系。
这次尝试比成功引发日本工业化的明治维新早了近10年。但半个世纪过去后,清王朝的努力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宫廷债台高筑,国家风雨飘摇,希望中的工业体系无影无踪,神州大地仍旧满目疮痍。
难怪中国在1894年的**次中日战争中被日本海军击溃并被日本榨取了天量的战争赔款。就像早期与英国的冲突一样,这次战争以中国的彻底失败和奇耻大辱告终: 甚至半工业化的小小日本都大大强于没有工业化的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偌大中国。13
清政府的无能引发了社会的长期动荡和人民对政治改革的诉求,并*终引发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摒弃了“榨取性”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中国历史上**个基于西方宪法的“包容性”政府。
由于清政府在中国现代化与应对外来侵略中半世纪之久的努力高度无效,革命因而发生。对清王朝统治的民族怨恨也加速了革命的发生。这是比英国光荣革命更为彻底的真正的革命。
它不是简单地限制清王朝的权力(像英国光荣革命那样),而是干脆完全彻底地废除了它。新共和政府试图通过全面模仿美国的民主、分权(即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三分)的政治制度来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
中国那时***的口号是“民有,民治,民享”,和“只有科学和民主才能救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革命者认为清政府工业化失败以及中国的长期落后是由于其缺乏民主和一个包容性、多元化的政府(正如制度学派所主张的那样)。
国民党建立了一个开放的包容的(甚至包括共产党的)联合政府,包容性的共和政府甚至接受共产党员。比如在1920年代,年轻的(共产党***)毛泽东曾经成为共和政府的**官员。并建立了现代企业、新的私有财产法律和从未见过的公立大学。
这个政府鼓励自由贸易,欢迎外国资本,并且在中国全面推广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小资产阶级尊严”(引用McCloskey),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商业城市。但40年之后的1949年,就平均生活水平和预期寿命而言,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穷的国家之一。14
中国第二次工业化尝试的失败也解释了为何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能够在1937年对中国几乎毫不费力但*度残暴野蛮地大举入侵。南京大屠杀就是见证。15
民国政府对解决中国贫穷问题和国家和平与统一的无能,使其在1949年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推翻。在6亿赤贫农民的支持下,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并且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尝试——这次是通过模仿苏联的计划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和民主。
30年过去了,这个尝试再次失败: 在1978年,中国本质上仍然困在同样的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中,人均消费与收入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没有显著差别。16
第三次工业化失败导致1978年邓小平的新经济改革——中国120年来的第四次工业化尝试。17
中国工业化速度令世人惊奇: 图为北京现代汽车工厂,机器人高效造车50秒完成车身焊接
轰隆!这次却“意外”成功了,并震惊了世界(包括中国自己)。其冲击波仍在全球回荡并猛烈撞击着世界各大经济体的投入产出结构。这次由13亿人一起引爆的工业革命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和全球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
随着中国对原材料和能源的巨大需求并进入全球商业网络,中国正在动员与推动整个亚洲大陆、拉丁美洲、非洲甚至工业化的西方前行。中国崛起给全球经济力量带来的冲击力是19世纪末美利坚合众国上升时期的20倍,19世纪初大英帝国爆发时期的100倍。18
一个简单数据就可反映这个冲击波的大小。仅仅看看中国的水泥生产和消费量,因为它是工业革命以来*基本的工业和建筑材料之一: 美国在1901—2000年总共消费了45亿吨水泥;中国在2011—2013年就消费了65亿吨水泥。中国在这三年内的水泥使用量比美国整个20世纪的使用量还多出50%。19
中国崛起给世界的启示与本书的写作计划
但中国崛起令人惊讶的地方不仅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闪电般的速度,或那自从17世纪以来一直困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规模金融危机的缺席,以及对于重大政治事件与国际金融动荡的成功躲避与处理(例如,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的戏剧性崩溃,156 0190 260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汶川大地震,与2008年以后的全球衰退等)。
中国崛起令人惊讶的地方,还在于她的和平与文明方式。20中国有近20%的世界人口,但只有6%的世界水资源与9%的世界耕地(目前中国的人均耕地不到美国的1/10,土质也是如此)。
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曾在这样的挑战下,单单通过互惠的国际贸易实现工业化和粮食自给,而不是重复西方工业强国当年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隶贩卖,以及对弱国发动血腥侵略战争的发展老路。
如果有什么窍门的话,中国完全依靠了她自身的商业头脑、实用主义精神、现成稳定的政治制度和*好的老师——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和中国过去的失败经历,而不是依靠当下流行的经院式的“黑板上”的西方经济学理论。
这样特殊的发展道路与成就值得相应水平的智慧鉴赏和公正评价。中国不是,也不该被视为人类经济发展史的一个特例或经济学理论的例外。中国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地理面积近似欧洲,把她当作经济发展的特例或例外太不可信了。
相反,中国的实践为重新思考整个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重新解读工业革命的机制本身提供了一个鲜活案例和千载难逢的机会。21
因此,本文的目标是双重的:(1)刻画与解释中国自1978年来快速工业化和社会经济变革的关键步骤与“诀窍”;(2)用中国的经验照亮知识界长期悬而未决的“英国工业革命之谜”。
本书将通过一个称为“新阶段论”或“胚胎发育”理论的理念框架,来解释经济发展的核心历史逻辑,这一逻辑在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增长奇迹的历程中一以贯之。
通过这样的尝试,我也希望解答**经济史学家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在其名著《国民财富与贫困的起源》中提出的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是在评论格申克龙(Gerschenkron,1962)**的通过在落后国家采用资本密集型现代企业实现跳跃式发展的理论时提出的:
在那些缺乏资本和熟练劳动力的原始落后国家,如何创造现代资本密集型工业?它们如何获得相关的高科技知识和管理技术?它们如何克服妨碍这些现代企业运作的社会、文化和体制障碍?它们如何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和制度?它们如何应对各种剧烈的社会变化?
这些问题发人深思。因为格申克龙基于19世纪中叶以后德国和俄国迅速工业化的经验所错误归纳出的发展理论,或由类似思路衍生的各种学派变体——例如进口替代策略,大推进理论,休克疗法和基于华盛顿共识的结构调整计划,直至当下流行的新制度经济学,使太多发展中国家不断误入迷途、陷入困境。22
这些发展策略和理论尽管看起来各不相同,却有着关键的共同点: 它们都把屋顶当作地基,把结果当作原因。它们把西方工业化的成果当作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它们教导贫穷的农业国通过建立先进的资本密集工业(如化学、钢铁和汽车工业),或建立现代金融体系(例如浮动汇率、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以及国有资产和自然资源彻底私有化),或建立现代政治体制(如民主和普选制)来开启工业化。
的确,当可以建立一个现代化汽车装配线时,何必重复18世纪英国的纺织作坊?当可以复制现代华尔街资本主义时,何必模仿19世纪美国的老式重商主义?当可以享受民主时,何必经历专制?当可以享受新潮的性解放的快乐时,何必要求保持传统的家庭结构与婚姻方式?23
然而,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发展经验(甚至她之前的失败教训)完全否定了这种关于经济发展的幼稚理念以及对现实世界如何运行的看法。中国的经历(好与坏,乐与苦,成与败)表明,正确的经济发展顺序和步骤,基于一国初始政治经济条件的实用主义的工业政策和发展战略,十分关键。它们不只关系到许多个人的福利,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存、尊严和命运。
工业化不只是企业层面生产技术的变革,更是民族国家的振兴。它要求所有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大协调,并动员所有草根阶层(特别是广大农民)和一切自然、社会、政治资源。错误的发展战略和工业政策会对一国造成灾难性甚至是无法逆转的后果。对于这一划时代历史重任,自由市场无法单独胜任,民主不是解药良方,全面私有化和金融自由不是正道,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也不是诀窍。
为什么?在我们开始讲中国的故事之前,值得再次强调的是中国自1978年改革以来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预料和计划之外的,是反复试验“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因为没有现成的经济理论可以告诉中国如何前进。24
即使这样的理论和建议在西方确实存在,中国也明智地拒绝了盲目采纳它们(不像非洲、拉美、俄罗斯和东欧所做的那样)。中国1978年以来的发展路径是崎岖不平的。毋庸讳言,中国政府犯过许多的错误。
然而幸运的是,尽管这些错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必要的痛苦,却都不是致命的错误(不像苏联的改革那样)。在不断试验和试错的过程中,邓小平及其政府做出了许多英明的决策,而这些决策后来被证明是促成久违的经济起飞和引爆中国工业革命的关键所在。
就像制度学派和自喻为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的张五常恰如其分指出的:我可以在一星期内写成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那么多的不利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情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25
然而,通过考察中国过去35年走过的历程和西方工业革命史,我们可以来试图回答戴维·兰德斯和张五常提出的问题。我们将清楚地看到,尽管初始的社会、经济、文化、制度、国际环境截然不同,中国的发展道路其实与两百多年前的英国工业革命遵循相同的内在逻辑。
在政治上层建筑与制度话语辞藻的表面差异之下,中国的发展模式,究其实质而言,与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和20世纪的日本是相通的,遵循着类似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规律。
注释
1: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78年12月召开,因此真正的改革开放到1979年才开始。本书完稿于2015年,采用的多数中国宏观数据截至2014年底,因此我们沿用35年这个约定俗成的整数大致作为从改革开放后到2015年的发展时间。另外关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工业化成就与改革开放后三十五年之间的关系,后续各章的很多地方都有讨论和阐述。
2:见D.Acemoglu and J.Robinson,2012,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Crown Business, 2012.(中文译本: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
3:见本书后续章节的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麻省理工学院教授Acemoglu和Robinson在其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认为缺乏民主(或包容性政治制度)是世界所有贫穷和停滞的根本原因。
例如,他们不仅赞同埃及茉莉花革命期间解放广场抗议者的观点,认为“埃及贫穷是因为它被少数精英阶层统治。精英阶层为了自身利益组织社会,而牺牲广大民众的利益”。他们还认为“(解放广场的人们)对埃及贫穷的这种解释为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找到了贫穷的根源……提供了普适性的解释”。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里通篇都企图说明一个理论观点: “所有穷国贫穷的原因与埃及贫穷的原因相同。”(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p.3)然而,这种理论不能够解释19世纪中后期德国和俄国在非包容性政治制度下的迅速崛起,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休克疗法经济改革的失败,自1978年起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下的增长奇迹,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快速的工业化,60年代到80年代韩国的经济起飞,以及新加坡独立后的增长奇迹。这并不令人吃惊。
这种理论甚至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政治制度相同的同一国家的不同地方(例如,芝加哥或圣路易斯这样的美国城市),有的社区*端贫穷,有的*端富裕,有的充满暴力犯罪,有的崇尚文明并遵从法治。
这种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意大利南部明显比北部贫穷,为什么17~18世纪的荷兰比英国拥有更自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却无法开启工业革命。因此,难怪大多数经济史学家们对于制度学派关于工业革命的解释持反对意见,可见Robert Allen (2009),Gregory Clark (2007), Deirdre McCloskey (2010), and Kenneth Pomeranz (2001)等。
4:美国学者和华盛顿政府智囊Joshua Muravchik认为,“军事征服常常被证明是移植民主的有效手段”。类似地,伊拉克战争的积*支持和辩护者,美国新保守主义学者和华府智囊Michael Ledeen也说,“人类历史上所发明过的*好的民主推广方案就是美国军队”(参见Greg Grandin, 2006, p.227)。
5:讽刺的是,在2011年推翻了独裁者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并开创了“阿拉伯之春”之后,突尼斯经历了4年经济停滞。而这之后,在2014年12月22日,88岁的突尼斯旧独裁政权前部长埃塞卜西(Beji Caid Essebsi)先生赢得了**次国家总统的民主选举。原因很简单,民主不能当饭吃,和经济发展无关。企图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结束腐败和贫穷,民主制度和糟糕的独裁政权一样无效率,而且更容易滋生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
事实上,自2011年起,突尼斯已成为滋生圣战者的温床,并且成为伊斯兰国(ISIS)与叙利亚、伊拉克*端组织外国武装分子的*大来源(见http://www.baijiantest.com/world/2014/oct/13/tunisia breeding ground islamic state fighters)。因而,在发展中国家强行推行不成熟的民主,不仅导致市场失败(缺失),也导致国家能力失败(缺失)。就像我们在本书中将要说明的,一个强大的政府一直以来就是工业化进程中“市场创造”的核心力量。
6:历史纪录表明早在17世纪末光荣革命时期(奴隶贸易鼎盛的一个世纪之前),欧洲流向非洲购买奴隶的贸易品中就有大约3/4为纺织品(其中大多数为英国生产)(见William J. Bernstein, 2008, A Splendid Exchange: How Trade Shaped the World.pp.274\276)。
英国政府和商人非常明白——就像Jan Pieterszoon Coen(一个**的荷兰商人和军官,巴达维亚的创立者,以及17世纪早期连续两任印尼东印度公司的主管)在1614年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可能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开拓贸易,也不可能在没有贸易的支持下从事战争”(Stephen R. Bown, Merchant Kings: When Companies Ruled the World, 1600\1900.Macmillan, 2010, p.7)。
大多数经济史学家都同意“作为(当时)政治和经济上*为成功的国家,英国在海外殖民地事实上的垄断地位,是其将原始工业化推向工业革命的核心前提条件”(见Kriedte, Medick, and Schlumbohm, 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 1977, p.131)。另外,经济史学家Pomeranz和Topik提出鸦片贸易“不仅使得英国取得了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同时也使其获得了对印度更大规模的顺差。没有这些盈余,英国不可能保持西方主要消费者和融资人的地位,而整个大西洋经济的成长将大幅度地减缓”(K. Pomeranz and S. Topik, 2013, p.104)。
7:关于从新古典模型角度对工业革命进行解释的努力,可见Desmet and Parente (2012), Hanson and Prescott (2002),Stokey (2001)和Yang and Zhu (2013)等。这些模型试图捕捉经济发展某些方面的重要特征,但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而供给能够自动创造与之相应的需求。这些模型忽视了与市场创造和劳动分工相联系的社会协调问题,忽视了市场需求对刺激供给和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也忽视了国家意志(政府)和其他因素在市场创造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因此,这些优雅的数学模型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来说仍然是一纸空文,无法付诸实践。
8:《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章家敦,因其在过去几十年反复预测中国崩溃而闻名。类似的书和文章很多,对中国崛起的悲观预测在西方媒体中仍是主流,尽管这种预测反复失败(如,*近的一篇文章出现在美国2015年3月2日的流行双月刊《国家利益》上,题为“大限: 迎接中国的崩溃”,参见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doomsday preparing chinascollapse\12343 )。
9:印度新任总理莫迪承诺“使21世纪成为印度的世纪”。印度能成功吗?需要具备什么条件?(见接下来的分析)
10:参考R. Allen (2009), D. Acemoglu and J. Robinson (2012), G. Clark (2007), D. Landes (1999), R. Lucas(2003),D. McCloskey (2010), J. Mokyr (2010), I. Morris (2010), D. North (1981), K. Pomerranz (2001)等。
11:重商主义是一种把国家的繁荣和强大建立在商业和制造业基础上的“经济民族主义”。它试图通过限制制造品进口、鼓励制造品出口而使国家富有。简而言之,它强调并推动制造业而不是农业,推动商业主义而不是重农主义。
然而,大多数重商主义文献只把它看作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和对外汇储备的盲目崇拜,而忽视了它重视商业与制造业的核心论点。一个仅仅依赖农业的经济无法受益于重商主义和外汇积累。但一个试图建立在制造业之上的国家却可以从重商主义中大大受益,因为制造业能促进劳动分工,形成规模经济。
在16~18世纪的欧洲,重商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原型与开启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步骤,其历史重要性不容忽视。
事实上,不像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841)那样,古典经济学家们,包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在内,很少重视重商主义固有的促进制造业的思想。
重商主义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一个例子是,19世纪基于“美国体制”思想的美国工业革命。“美国体制”是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在1791年构想的突破美国传统农业“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并在整个19世纪获得美国政府积*落实,让美国制造业和对外贸易赢得了与英国的全球竞争。
“美国体制”包含几个相辅相成的部分: 高关税保护和促进美国北方新兴制造业;建立国家银行促进商业、稳定货币控制私有银行的风险;维持公共用地的保护和垄断高价,以获得联邦收入;对道路、运河与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补贴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即通过关税和土地销售来获得政府融资。
张夏准(2003)《富国的陷阱》一书中有许多关于重商主义及它在西方经济发展中的历史角色的例子。然而问题在于,许多拉美国家在20世纪中叶也采用了多种形式的重商主义(例如,进口替代工业化)但遭到惨败。这成败的原因正是本书要探讨的内容。
12:基于“榨取性”与“包容性”二分法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参考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5, 2012)。
13:技术重要。尽管南美印加农民数量是西班牙士兵的几百倍,配备枪炮、病菌与钢铁的西班牙士兵轻松击败了无组织的印加农民。然而,赢得战争或征服一个农业国,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工业化使国家具备人力组织资本与后勤能力,以保障组织军事力量并源源不断地供给战争所需的后勤经济资源。
14:在1949年,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的份额仍高于90%。人均收入自1860年起变化不大。平均预期寿命仍为30~35岁。
15:参见张纯如,《南京暴行: 被遗忘的大屠杀》。西方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录和资料,参见
http://www.nanking massacre.com/rape_of_nanking_or_nanjing_massacre_1937.html
和http://www.csee.umbc.edu/~kunliu1/Nanjing_Massacre.html,及其中提到的参考文献。
16:确切而公平地说,每次尝试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不足以引爆工业革命。例如,在第三次尝试中,中国建立了基本(尽管高度亏损)的工业体系。工业高度依赖来自农业重税的政府补贴。
然而,农业生产率显著提高(除了“大跃进”期间),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35岁显著提高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68岁。婴儿死亡率由25%大幅削减到4%,中国人口疟疾率由5.5%下降到0.3%。毛泽东时期的工业化建设和农村合作化运动对于邓小平时代引爆工业革命的意义会在以下章节继续探讨。
17: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与埃及等非洲国家应该很熟悉这些周而复始的“启动—停止—再启动—再停止”的恶性循环。
18:英国人口在1810年约1000万,美国人口在1890年约6000万,中国人口在1980年是10亿,在1995年达到12亿。
19:见http://www.gatesnotes.com/About Bill Gates/Concrete in China。
20:对于这一点,广大非洲人民深有感受。
21: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Acemoglu和Robinson(2012)把中国的增长奇迹归因于其严重的落后及与前沿工业国巨大的技术差异(即所谓后发优势)。但所有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与挥洒在“为什么国家失败”问题上的墨水,都是为了解释为什么落后国家尽管落后却无法实现增长;为什么中国却在1978年之后神奇地获得了(释放出)这种“后发优势”?。
22:Gerschenkron (1962)认为由于工业的规模与技术复杂性持续增长,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越来越依赖中央政府的帮助与强大的制度工具,以调动产业融资来赶上发达国家。他这种关于政府作用的观点是对的。
然而,他认为追赶的方式是通过国家银行全力扶持现代高效前沿技术,建立现代重工业,并全方位推进工业化。
这个建议是不正确的和本末倒置的。这一发展战略不仅仅是违背了林毅夫讲的“比较优势”,而且违背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这一古典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但是亚当·斯密忽视了创造市场的巨大社会成本,国家意志和政府在创造市场中的关键作用,和“市场本身是一个*基本的公共产品”这一根本原理。
23:美国总统奥巴马2015年“衣锦还乡”访问非洲时,站在中国修建的大楼里重点强调非洲的同性恋权利,却不谈贫困的非洲人民在被欧洲殖民者掠夺几百年后,仍未在衣食住行方面获得基本制造能力的根本问题。
24:见B. Naughton (1995)和吴敬琏(2005)对中国改革过程的描述与分析。
25: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