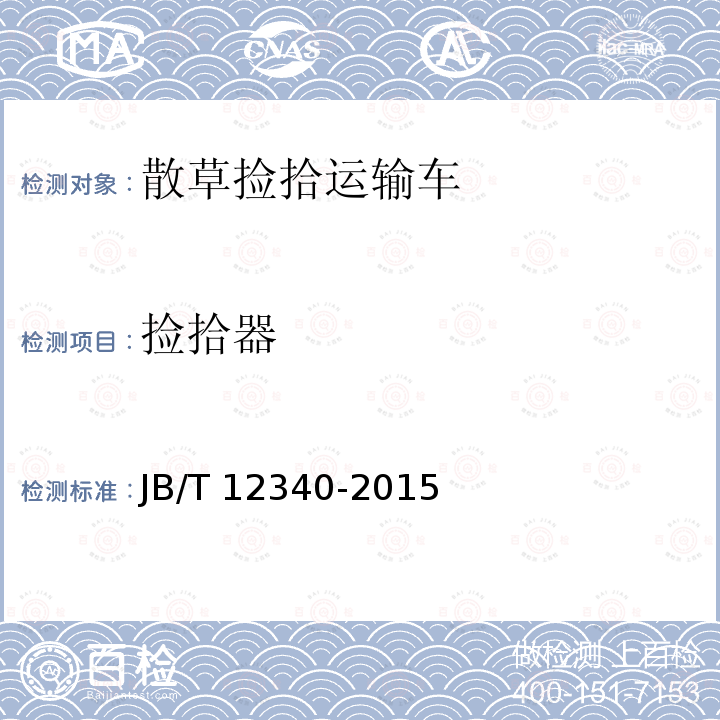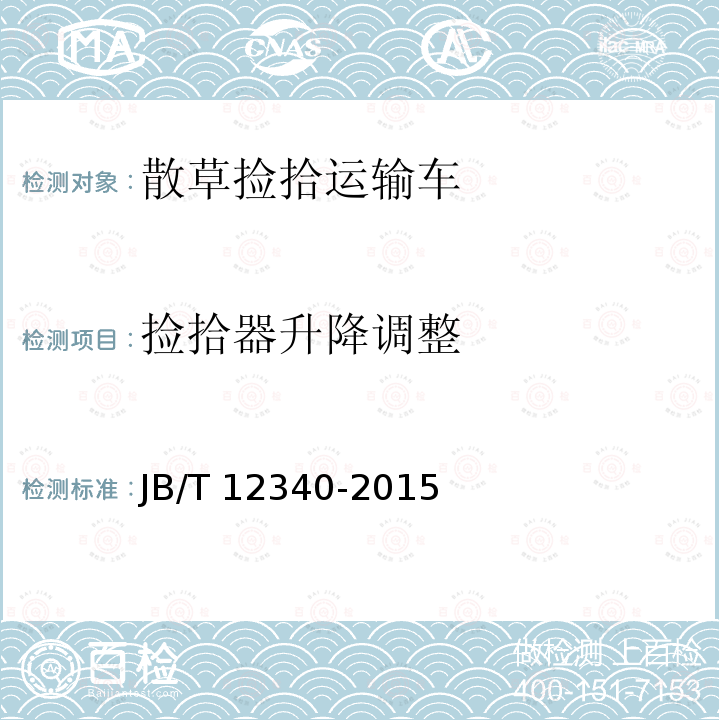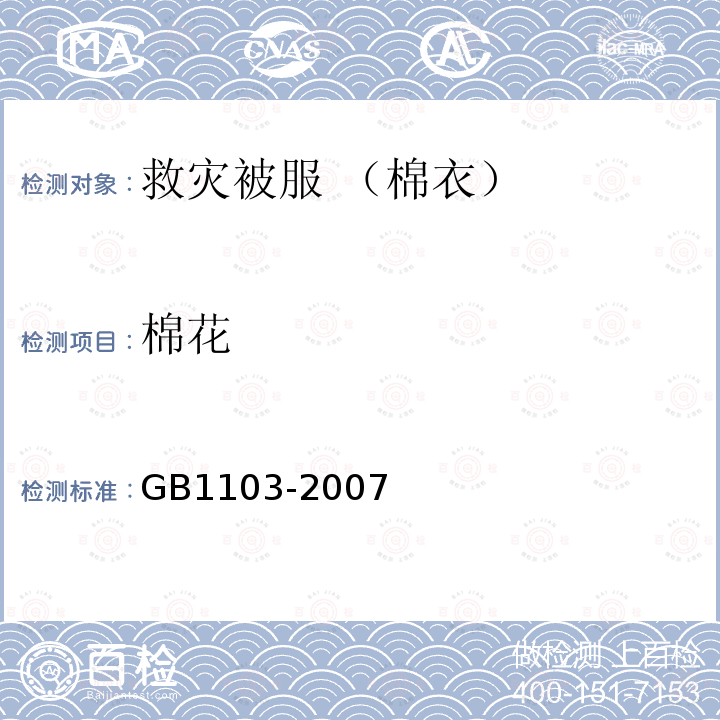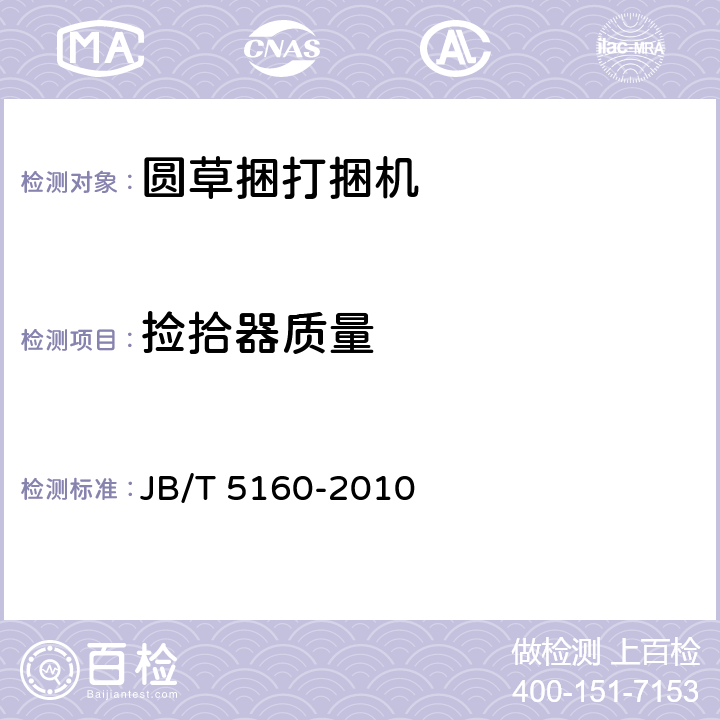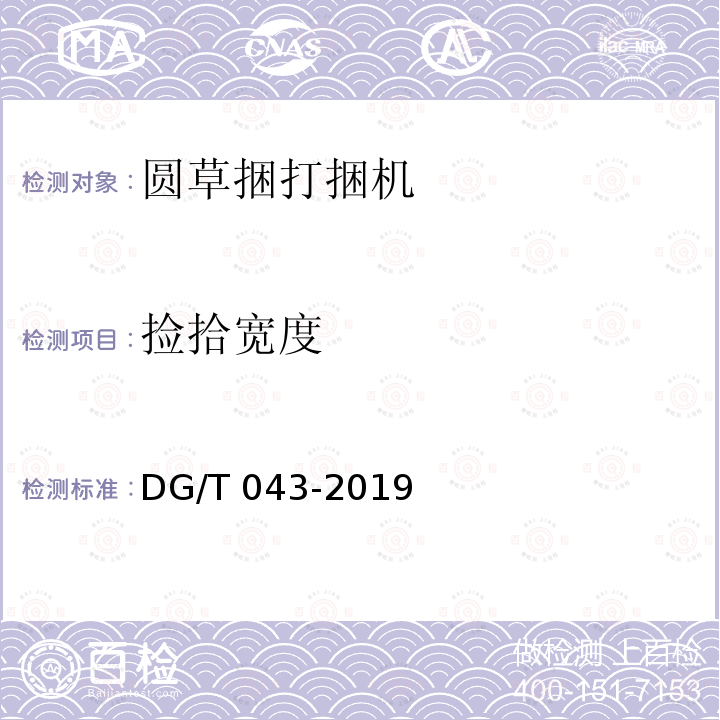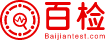深秋,站在家乡的田埂上,大片雪白的
刚从学校里放学回家,走在田埂上,就被正在棉田里拾棉花的母亲叫住了。母亲隐藏在高高的棉花丛中,只露出一顶草帽来。其他同学都被自己的父母叫去拾棉花,我不想去也不行了。我正要把书包里的书倒出来,母亲说,不用你的书包,你父亲的布囊还在地里呢。我拨开密实的棉株,来到母亲的跟前。只见,母亲怀中的布囊鼓鼓的涨起,一副大腹便便的样子。虽然已是深秋,但高悬的太阳还是有点热烈的,母亲的脸上汗津津的闪光。我瞅了瞅,问父亲呢?母亲说,你父亲没有心性,只拾了一小袋棉花就说有事走了。父亲是个泥水匠,经常要走村串户外出做事,这也不能埋怨了父亲。但说父亲是个没有耐性也是对的,父亲不甘于手上这种枯燥而无趣的活,轻盈洁白的棉花还是比较适合于女人的身手。
我把父亲的布囊系在腰上,母亲要我和她做搭手,分别站在一垄棉花的两侧。母亲身手敏捷,三指往前一伸,左右开弓熟练地采拾身边的棉花。一会儿,手里满了一大把,才放入怀中的布囊里,收获的幸福写在母亲脸上。棉花像雪花一样轻盈地附着在棉树上,茸茸蓬松的样子。而我伸手去摘,却难免会碰到如刺一般的虬枝,扎得人的手生疼,双手也会被划出一道道白白的划痕。傍晚时候,怀里的布囊里已经装了不少棉花,蓬松而又沉重,秋阳一晒,一股芳香的太阳味扑鼻而来。母亲把布囊里的棉花规整好,踏在弯曲的田埂朝家中走去。
拾棉花的季节里,不少棉株上还开着一些白的、红的花儿,薄如蝉翼的花瓣在秋阳下,格外得显眼,也算是田野里一处独到的风景。有的枝头上则刚刚接了一个青涩的小棉桃,用不了多久,就会吐放出雪白的棉花来。棉花拾了一茬,又会长出一茬来,所谓“拾不尽的棉花,打不完的芝麻”就是指此了。真正摘完棉花,要到初冬。那时,气温低,棉花也就不会再接桃了。棉农们才把棉秆连根拔了去,晒干当柴烧。
其实种植棉花是很烦琐的,从下种到育秧,再到结出花蕾,棉农人还得给它掐枝打杈,给它治虫防病,不知要经历多少道工序,棉花也知报恩似的,开了一茬又一茬,从初秋一直延续到严寒的冬天。棉花恰是一种高洁的沐浴、坦荡的给予。棉农们起早贪黑,不就是为了这雪白暖意浓浓的棉花吗!
寒冬来袭,母亲又坐在灯下,为我们缝制御寒的衣物。那雪白的棉花成了我们身上的棉衣棉裤,还有那厚厚的棉鞋,整个冬天也都不会冷了。棉花是这么亲切和暖意,让我由衷感觉到一种幸福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