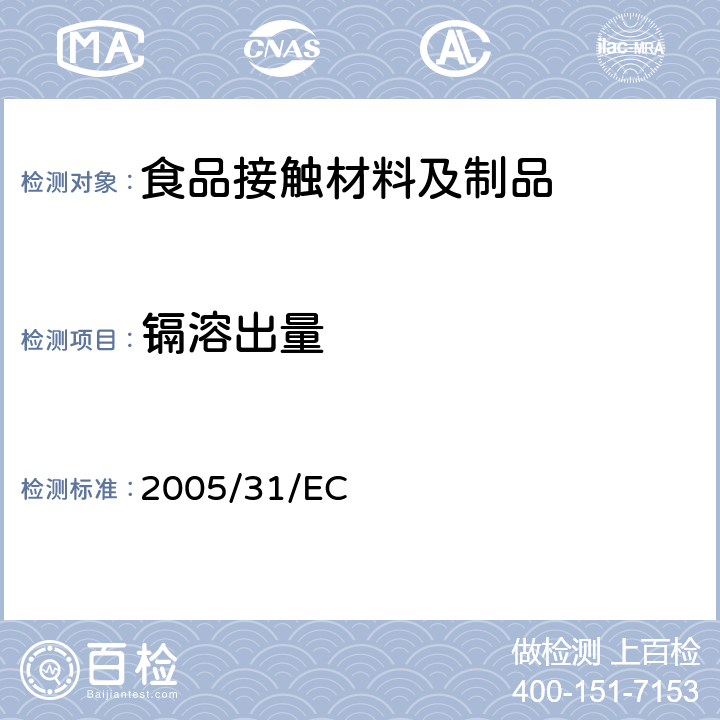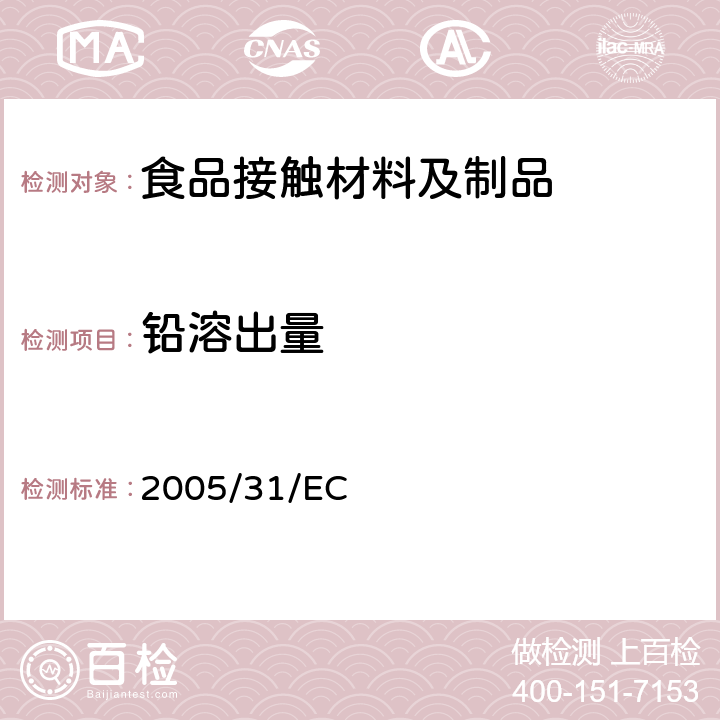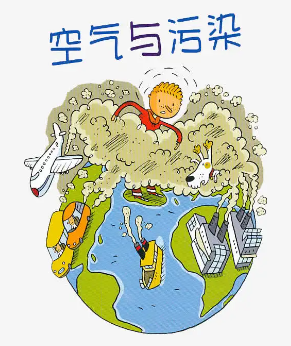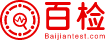?? “温州不行了”的*直接证据就是在浙江省公布的2002年统计数字中,温州的GDP增速出人意料地滑落到第七位;进入2003年更是每况愈下,上半年名列全省倒数第二,7、8月份则连续两月倒数**。在不少热心人士的共同努力之下,“温州模式”被找出了“两大软肋”:其一是经济发展基本依靠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吸引外资能力*为有限,产业结构升级过于缓慢;其二是随着民营企业在当地的日益密集,土地、人才等资源的约束效应显现日甚一日,造成资本大量外流、企业成批外迁,产业空心化现象加剧。这样一来,在“温州模式”与其老对手“苏南模式”的较量中似乎终于要“风水轮流转”了。
??基本面仍然是好的
?? 在“温州模式”受到普遍追捧的日子里,温州人不少被挖掘出来的生意秘籍到今天仍然有被重新回味一下的必要——“温州人有10万元,绝不会像外地人只用5万,留5万备急,他不仅把10万全投进去而且还借款,以便在市场上尽力获得竞争优势。”;温州家庭企业出于对家族成员的信任,决策非常快,承担风险能力很强。他们做生意完全是有利就做。”;温州老板大多从事**线生产,不少老板扮成打工仔去深圳的台资企业学成本控制;正泰集团南存辉讲起当年办集团企业的故事:“政府一直要我搞企业集团,我不干,因为我想不通有什么好处。”
?? 从这些凌乱的经验归纳之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温州的制造业企业是真正符合“产权清晰、权责明确、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竞争主体要求的,温州在改革开放中的产权制度改革是一步到位的,温州的经济增长都是以清晰的民间财产权为基础的“实”的发展。仅仅因为这一个缘由,我们就可以断定“温州模式”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继续代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不应该被轻易否定的。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没有理由根据短期内地方间经济发展指标的变化衡量发展方向正确与否,更没有理由用GDP这种无法反映制度变迁程度的指标去给从不同起点上起跑的地区列队排序。
??两个可以解决的问题
?? 在各地以重化工业为先导的新一轮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热潮中,温州以服装、皮革、打火机等传统制造业为主体、依靠自身积累循环发展的产业结构自然不如以前“风光”了。然而,急于断定“温州模式”就一定缺乏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却是有失偏颇的。由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过渡到重化工业、高技术产业固然是产业结构升级,依靠现代技术和管理手段重新组织传统产业的生产,也未必就不是产业升级。现在温州人无疑选择的是后一条产业升级的道路。正如温州市委书记所言:“我们的‘康奈’皮鞋一双可以卖到1000多元,现在1台25英寸彩电也就是1000多元,你说哪个的附加值更高?”有人认为,温州企业家几代人从事一种行业经营的特点限制了产业升级的动力,殊不知,这种“代际锁定”的执着性正是占领价值链高端的必要条件——品牌赖以形成的重要来源之一。事实上,温州现在以拥有7个全国驰名商标、15个中国**产品,是我国品牌集中度*高的地区之一。在这里,我们一定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观念,那就是现代经济一定要搞大企业、上高新技术行业。事实上,小企业通过良好的分工协作一样占领大市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能带来高额的利润。顺其自然、因地制宜是各地选择产业结构的*佳选择。
?? “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所谓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设计的结果。事实上,这两种模式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市化形式。在促使资本与农村廉价劳动力结合、通过大力发展制造业提高居民收入这一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选择上,这二者则是完全统一的。只是由于苏南地区工业基础相对较好,对外交通方便,知识人才相对密集,故而倾向于选择外来资本,组织形式也以创办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改制为主。而温州所在的浙南地区在自然资源、基础设施方面的条件相对较差,但当地居民的经商创业意识从来很强,通过自主的资本积累力推民企发展也是非常自然的。这两种模式如果异地而处,很可能都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那种承认一个就必须否定另一个的事前判断也是站不住脚的。
?? 至于资本外流和企业外迁,则的确是温州经济面临的真正挑战。不过我们也应该同时意识到,这些都是经济发达地区在资本积累达到一定数量、企业形成相当规模之后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缺少了流动性,资本根本就不能再被称之为资本。当资本和企业数量在特定区域内密集到了一定程度时,生产成本必然上升、投入的边际收益也会经历下降的过程,转移就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如何把握这一过程。日本一直为制造业向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转移加剧了本国的“产业空心化”而忧心忡忡。然而,近两年以来日本外资流动顺差超过了对外贸易顺差的事实,客观上促使日本认真思考如何利用依靠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汇回的营业收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样,在全国众多地区把目光盯在衡量本地产出的GDP上的时候,包括温州在内的浙江不少县市越来越多地提到地方永久居民投资、生产成果的GNP概念。的确,如果采用GNP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温州经济在全国所占的位置无疑会更加重要。企业外迁以后,如果和原驻地彻底断绝联系,则肯定造成产业空心化。但这种转移同样可能促使资本流出地向金融等商务活动中心转型,并向更高领域的服务业进军,造成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携手发展的双赢局面。当然,这要求有高质量的人才储备、便捷的信息交换方式和完善的公共服务作为保障,而这些才是“温州模式”在未来的着力重点所在。
?? 为了温州,也就是为了中国经济的未来
?? 承认“温州模式”的成就甚至是优越性并非否认其缺陷所在。然而这些缺陷往往并非由温州自身产生而来,而是反映了我国宏观经济结构中许多仍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因而也并非是温州一家能够独立解决的。例如,“温州炒房团”因为制造了房地产泡沫而广受诟病,但这恰恰反映了在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在内的众多投资领域不向民间资本开放的条件下,民资严重缺乏合理的获利空间,呼唤的是政府降低民间资本准入的门槛;温州民间资本充裕而许多企业却面临“贷款难”,地下金融一度十分猖獗,这就要求政府在批准设立民营银行、更充分利用股票市场等现代金融工具方面的步子要迈得更大;“温州模式”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放手让民间经济力量自主创新,而自己处于“缺位”状态,现在民间资本开始热衷于钢铁、汽车等投资多、获利快、风险大的行业,对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目的企业来说这本无可厚非,但却加大了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政府的“缺位”状态不能再持续了,迫切需要政府对民间投资进行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引导,真正考验政府宏观调控水平的时刻到了。
?? 温州人在改革开放之初大胆开拓创新,充分利用“制度落差”快速推进了现代化进程,却也因此提前遇到了众多新问题、新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是其他地区迟早要碰到的。因此,解“温州模式”之困决非温州人自家之事。